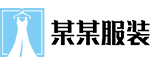“一早起床,两腿齐飞,三洋打工,四海为家,五点下班,六步晕眩,七滴眼泪,八把鼻涕,九(久)做下去,十(实)会死亡。”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这首涂鸦在蛇口三洋厂厕所墙壁上的“诗”,被一位文化研究者发现。
那个时候的深圳,没有地王大厦、深南大道还是土路,站在这座尘土飞扬的城市,就像站在一个大工地里。
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,“三来一补”成为深圳主要经济模式,大大小小的服装厂、鞋厂、玩具厂、电子厂等劳动密集型工厂满地皆是。
百业待兴,简陋的罗湖火车站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外来务工者,他们有以一个共同的名字:“打工仔”、“打工妹”。
偌大的车间,狭窄的工位。白天,这些流水线上的打工青年们,重复着简单而机械的动作,下班便抱着餐具排队打饭。
没有电视机、没有录音机、没有手机,在那个逼仄的员工宿舍里,多数人的闲暇时间也很无聊。有时候,他们会结伴在路上漫无目的地游走,有时候挤在当地居民的窗口,“偷看”电视机里的香港节目。
在这个庞大的打工群体中,有一个名为林坚的小伙子,从高中时期就开始文学创作。1982年他来到深圳,第二年便开始创作自己的短篇小说《深夜,海边有一个人》。
1984年,林坚的这部小说发表在《特区文学》杂志的第三期,被视作“打工文学”最早的作品之一。在当时,这部小说并没有在文坛上荡起多少涟漪,却启发了无数个“林坚”开始写作。
那一年,邓公第一次视察深圳,为深圳题词:“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,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。”
1988年12月,宝安区文化局创办了第一本打工文学刊物《大鹏湾》。上面首刊了张伟明的一篇打工题材的小说《我们INT》。
“我抽空来到李树那堆小山般高的坏机前,这堆黑疙瘩除了贴有说明其它部件不良的字样外,都千篇一律地贴有INT(接触不良)的字样。我看一眼其他检验员,客家妹的红筒裙很刺目。这些检验员都无不例外紧绷着蜡黄的脸,都目不斜视地飞快地舞动着双臂,都有李树那种穿山甲的特征。”
“INT”,即接触不良的意思,是外资企业中常用的品质检验术语。作为一名质检员,张伟明笔下的人物与卓别林的《摩登时代》无异。
在这条永不停歇的流水线上,“接触不良”的不仅有坏机,还有麻木的工人。他们成为了大机器生产中的一颗螺丝钉,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有严格规定。疯狂的机械劳作摧残的不只是身体,还有心灵。
“不一会儿我身边也堆起了小山般高的坏机,坏机身上无一例外地贴着INT字样!妈的,这样子干下去我们每个人迟早也会INT。”
其实,1964年出生的张伟明,是最后一批毕业后能够分配工作的高中生。在老家的蕉岭县锰化厂拿着“铁饭碗”,是令人羡慕的工人阶级中一员。但为了追求自己的文学梦,23岁的他坐上了开往深圳的长途汽车,流浪半个月找到第一份流水线工作。工人、质检员、领班……底层的生活经验也成为他创作的源泉。
1991年,一部讲述改革开放初期打工妹生活的电视剧《外来妹》在央视热播,掀起一阵收视狂潮。
在深圳,这些年龄在18-25岁的打工妹虽然文化程度不高,却比男性更有耐心和细心,深得大部分工厂青睐。其中,不乏边上班边学习的女孩子,安子,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在深圳打工的七年,她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和积蓄都投入到学习中,并考取了深圳大学中文系大专班。1991年,安子的第一部打工纪实小说《青春驿站——深圳打工妹写真》在《深圳特区报》连载。
“当表姐带我到蔡屋围一家电子厂见工时,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件商品,在任人挑选。”
“流水线,有多少打工妹在用青春的舟揖泅渡这流水线?前面没有岸的呼唤,也没有航标灯的昭示。”
安子的打工小故事,既有个人的亲身经历,也取材于身边打工妹的生活。那种心灵鸡汤式的理想也让她几乎一夜间成为百万打工妹的偶像。安子也被称为“打工皇后”。也正是从此开始,打工文学真正发生了广泛的影响。
其实,在90年代前,打工文化在文化界一直只作为一种现象被探讨,且被称为“打工仔文艺”。准确来说,直到1991年,深圳青年文学家杨宏海在《打工世界与打工文学》一文中才提出“打工文学”这一命名。
1992年,深圳宝安石岩镇的打工诗人郭海鸿创办了《加班报》:“我们刚刚结束给老板的加班,现在我们开始为自己的命运加班。”
那一年,深圳火车站的绿色专列走来一个88岁的老人,无数梦想都在那个夏天发酵。
2000年8月,“大写的20年·打工文学研讨会”在深圳宝安举行,那是首次全国性的“打工文学”研讨会。
也正是从90年代至2010年前后,“打工文学”从萌芽期跨越到迅速发展的阶段,涌现了一大批知名的打工作家。
来自湖北荆州,只有初中文凭的王十月表示,从2000年到2006年,在深圳的六年是自己的精神胎记。他在自己的自述文章《我是我的陷阱》中写到:
“打工近二十年,我一直努力做的一件事,就是脱离打工阶级,努力融入身处的城市。我并不觉得城市代表恶、乡村代表美,处处有恶,处处也有美。”
同样是初中毕业的湖南平江人戴斌,1994年来到深圳打工。当过搬运工,蹬过三轮车,卖过豆腐,编过内部刊物,办过职介所,干过推销员以及自由撰稿人的他是个高产的“打工作家”。
“深南大道像天堂一样美。小菊对表姐这句话深信不疑,她虽然不知道天堂有多美,但关于天堂的神话她是看过的……”
可惜,他笔下的小菊为了获得边防证搭上自己的性命,最终也不知道自己梦寐以求的深南大道有多美。
相比90年代,进入21世纪的深圳已经焕然一新。皇岗口岸24小时通关,深圳地铁通车,深圳湾大桥通车……深圳速度,一直在刷新。
2013年,一个名为郭金牛的47岁农民工,被一位荷兰诗人索要签名,那是在一个国际诗歌颁奖典礼上,这个农民工的诗集《纸上还乡》获得了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诗集奖,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主席巴斯给他颁奖。
2010年,富士康发生了令人扼腕痛惜的“十三连跳”,那时候被派去安装“防跳网”的正是在富士康打工的郭金牛。
他悲伤地发现,每次当他顺时针将螺丝拧紧的时候,都有一个年轻的灵魂在挣扎反抗。
2012年,一份深圳版的”欢迎体“海报引起了市内外的广泛关注:”来了,就是深圳人“。
那一年,一个名叫许立志的90后潮汕小伙子进入富士康,在流水线上已经工作了一年多。
2014年10月1日凌晨,年仅24岁的许立志从龙华一座大厦纵身一跃,离开了世界。生前,他的微博预设在零点零分发送出一条消息:新的一天。
当下,随着几十年经济的快速转型,机械化逐渐代替人工,个体的创作源泉无疑也在消逝。随着互联网工具的发达,他们不仅在流水线上写诗,不仅在杂志诗刊发表,每个人也可以在微博、微信、视频网站等平台写段子、写心情。
这些弥足珍贵的文本,是深圳这座城市与打工一族个体命运的共同记录。写作、写诗,也许就是他们活下去的动力,有的人借此改变了命运,名利双收;有的人依然在原地,疼痛着成长;有的人,只留下了诗便远去……
这个群体是卑微的,很多人的呐喊并没有被听见;这个群体是伟大的,深圳40年流淌着他们的血汗。
“打工文学”是时代特殊的产物,也是文学界的一个传奇。这些漫长的、沉重的、真实的歌颂与批评,何尝不是深圳史上的绝唱?